任县铝合金门窗
文章目录:
1、谷文昌的兄弟情2、谷文昌的兄弟情3、走进白水系列——郭家庄
谷文昌的兄弟情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福建省东山县干部群众为缅怀和追思原县委书记谷文昌而立的谷文昌雕像。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一
1949年初的太行山,峡谷里的树大都光秃了,仍有几片红枫在枝头漫舞,抖擞着精神,像要与寒风再斗三百回合。
原平原省林县(今河南省林州市)石板岩乡郭家庄一处农家,烤红薯香味四溢。农民谷文德出口的话,却显得有几分苦涩:“哥啊,你为何要自愿报名……”
他们说的是家事国事天下事。这年元旦,毛泽东同志借新年献词发令“将革命进行到底”后,“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激昂口号,连同中共中央关于从老解放区选调5.3万名干部,分配到新区领导建设的决议,在太行山谷里回响时,在林县当区长的谷文昌二话不说就主动报了名。
“文德,今年必将是中国历史翻天覆地的一个分水岭,关键时刻,共产党员更应当听从党的召唤!”谷文昌烤着火,说得热血沸腾,像报名时那样,字字铿锵。
“不是说自愿嘛!”
弟弟的话,弦外之音不言而喻。大哥早已前往山西谋生落户,他着实舍不得二哥谷文昌再远行。更何况二哥留在家乡做事,全家人还能经常见面。
33岁的谷文昌这个时候正值上有老下有小。母亲年逾六旬,在当石匠的父亲去世后备尝艰辛,身体一直不好,他南下的话必然难以尽孝;两个女儿大的不到10岁,小的还在咿呀学语……解放了,分田了,日子一天好过一天,祖祖辈辈梦想中的好日子刚开头,何必离家千里再奔波呢?
谷文昌说:“县委马书记、组织部蔡部长都带头报名南下哩。人家背井离乡来林县领导咱们闹革命,解放咱们之后又要随军南下,这是榜样哩!咱是共产党员,不能光顾自己,也要为党尽心,为江南老百姓的解放出份力!”
这番话如同钢钎凿石,弟弟的心扉终被撞出了火花,他知道哥哥有着比太行山巉岩还刚的犟劲、比峡谷云天还高的理想。想到亲如手足的兄弟情分,他为哥哥的壮志远行送上了定心丸:“好,你放心去吧,家里还有我!”
谷文昌就这样填写了“南征政民工作人员登记表”,在“家庭有啥困难”一栏里填上“没有困难”,在“家庭照顾的依托人姓名”一栏里写上“依托兄弟谷文德”。继而又联合6人向组织递交了一份写在烟盒背面的“保证书”:“每人家庭早有准备,不会拖后腿。阴历正月初九早饭集中十区署,保证当天下午报到平房庄。”
那晚给老娘洗过脚捶过背,第二天一早给小女梳过头后,谷文昌就打起背包,出现在了郭家庄的欢送会上。他在会上郑重表态:“我已下定决心,不解放江南老百姓誓不回来!决不给家乡丢脸,决不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
谷文德哪能知道:他的哥哥历时大半年、从中原腹地长驱3000公里,风雨南下,九死一生。躲敌机空袭,避特务黑枪,掩埋起战友的遗体又奋力向前。铁路遭敌破坏后,就靠双腿走路,滑倒了再爬起,血泡溃烂,脚底鲜红的肌肉与鞋底黏在一起,军装上印出一片白花花的盐渍。途中肺病发作,又经酷暑暴雨,高烧纠缠不休……
他更不知道,哥哥这一次远行,从体魄到灵魂都得以脱胎换骨,在进军福建途中所说的“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成了他一生践行的誓言。
图为东山岛风景。 胡东雄摄
二
福建在哪里?福建是什么样的地方?
1949年6月,谷文昌所在的长江支队到苏州后,才知并非留在苏州、上海,也不是拐个弯去大西南,而是继续南下去福建。明确最后的去向后,有人找来地图一看,不觉惊叫起来:福建偏远不说,连根红线(指铁路)也没有呀!有人还去书店买来相关图书,介绍福建的顺口溜很快就传开来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
不切实际的故事越说越玄,越说越使北方人犯怵。有人瞻前顾后,心里打鼓;有人犹豫不决,称病要求留在苏沪。谷文昌却一往无前,党指向哪,他就奔向哪。
接到兄长报平安的信后,谷文德便对福建省东山县那个海岛心心念念起来。1952年,他带着大侄女一路向东行,去看望据说已当了东山县县长的哥哥谷文昌。
几天几夜的火车,再换乘汽车,辗转来到东海之滨。从八尺门海峡坐船跨海,海浪颠簸得他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要是船能掉头,天边那个岛他可能就不去了。他想,一母同胞,哥哥在这孤岛进进出出,得吐多少回呢?
出现在眼前的县长哥哥,脚蹬布鞋,身着褪了色的灰中山装,绝非他在老家乡下所想象的“呢子大氅叫备用,迎来送往不发愁”的干部形象。那时候,哥哥在东山县当县长,嫂嫂当县妇联主任,所谓的家,就是在县长办公室里搭个床铺。他来了,只能和县委通讯员同挤一个门窗吱嘎作响的房间。
未见过大海的谷文德,幻想过东山的海岛风光,见到的却是个风沙呼啸的荒岛,心底竟有几分不信。晚上听得狂风呼啸,所居之屋就像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小舟,随时都会被风浪吞没,便问同住的县委通讯员:“你们这里的风沙咋这么厉害?”
通讯员回答他:“这还不算大,大的都能把房子整个给埋了。”
谷文德在东山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坐卧不安了,忍不住跟哥哥抱怨:“咱林县够艰苦了,没料到东山更苦!咱林县再苦,好歹树上叶子能吃,地里有野菜能挖,河里有水能喝。东山却到处光秃秃的,沙子能吃吗,西北风能吃吗,海水能喝吗?”
哥哥却说:“咱离乡背井不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吃上饭吗?共产党人不就是来救穷人的吗?”
来一趟不容易,哥哥和嫂嫂都希望他多住几天。可谷文德实在待不下去,别说海岛上无处不在的海腥味让他反胃,出门还得戴风镜,否则只能让风沙把眼睛打肿打痛。他感到难以适应,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风沙啊,怪不得东山的百姓称之为“沙虎”“风妖”!离开东山时,他带走了些小鱼干和虾米,带上了哥哥节衣缩食省下的一点钱。他觉得东山的条件太恶劣,能够建成哥哥说的美丽与富饶的地方吗?
三
谷文德回去不久,就听说东山发生了一场大战。如何个震惊世界,他不知道,只是听说毛主席表扬这是个大胜利,而且最欣慰的是,哥哥还活着!
新中国成立后,福建还一直是前线,与台湾一水之隔的东山更是最前哨。谷文德又开始为哥哥牵肠挂肚,没过几年,他又来到东山。
这次,他从老家带来了哥哥打小爱吃的山楂、杮饼。哥哥烟不离嘴,吃这些可以化痰,他一直都是关心哥哥的。他也照哥哥的吩咐,带来一把卸了柄的锄头,问:“你都当县委书记了,还要这把式干什么?”
谷文昌憨憨地笑着:“老家的锄头我从小用得顺手,今后走到哪里都带上它,既能就地劳动,也好提醒自己别忘本。”
谷文德握了握哥哥的手,伤痕累累,比自己的手还粗糙。
在和通讯员及东山干部群众闲谈中,他已然知道,哥哥这双手,攀过沙丘,打过石子,筑过堤,种过草,植过树,捏碎过一个又一个天大的困难!哥哥还雄心勃勃地发起了改造自然的造林治沙之战,屡败屡战,听说还当众立下誓言:“不把风沙制服,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样的官当得可真是苦,何必呢?他有不解,也有担忧。
但他又看到,与自己第一次登岛不同,东山变样了,不说昔日充斥于耳的风沙咆哮声变弱了,时歇时续了,水贵如油及燃料紧缺的现象也不再让人揪心。最引人注目的是,原来的濯濯童山、千里荒滩有了丝丝绿意。人在东山,其实也难见哥哥的身影,他不是下乡调研去了,就是在开会,要么是在参加劳动,终日不得闲。有天难得在饭间多唠几句嗑,雷声忽至,哥哥二话不说披上雨衣,拿起锄头就冲出了门。他从此知道,在这个地方,雷声就是造林的命令,雷声一响,“一呼百应”。他有次跟着侄儿冒雨奔向就近的植树造林战场,嗬,从四面八方向雨阵中奔来的,是无数的群众和学生,几乎人人都没穿鞋。谁都说:谷书记就在前面和大家一起种树哩!
谷文德感受到了哥哥在东山的威望,却也没忘记老母亲希望哥哥回故乡工作的愿望。回家前,他特地央求过兄嫂:“咱妈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来不了东山,你们干几年调回老家,不是一样为人民服务嘛,顺道也满足咱妈的一个念想……”
哥哥打断了弟弟的话:“当了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就是四海为家,听从党的安排,不管落在什么地方,都要在那里生根开花。你也入党了,该明白这个道理。”
那一次,哥哥陪着弟弟来到月光下的海边,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文德,你回去告诉咱妈,等东山像咱林县一样密密麻麻地长满了树,我一定回去好好服侍她老人家。你说中不中啊?”
月亮朗朗地照着兄弟俩。谷文德看见月光和海水一同在哥哥的眼里打转,闪烁得让他鼻子发酸。
四
谷文昌也不是忘情之人。那年观看潮剧经典戏《四郎探母》,戏里杨四郎有心过营探母,奈何关口阻拦,只能仰天长叹:“高堂老母难叩问,怎不叫人泪涟涟。”台下的谷文昌听得泪水直流,哽咽着对妻子说,不知道咱妈现在情况如何?
谷文昌真是有心把母亲接到东山来养老,但风烛残年的老人无法远行,只好节衣缩食接连寄钱寄物,有时让孩子们寒暑假回老家代为尽孝。
1962年2月中旬,谷文昌到北京参加大会,会后在回福建路上拐往大哥一家移居的山西长治市牛村,看望在这里过年的母亲。正值春节期间,他事先交代妻子带上孩子们从东山前来会合,弟弟也带着家小前来团聚。四代同堂,特地拍下了唯一一张家族合影。谷文昌夫妇和母亲住了一个来礼拜的窑洞,每晚都给老娘洗脚,听老人絮叨。
谷文昌欢迎亲人们去东山参加植树造林。弟弟心有余悸的不是苦和远,而是晕船,哥哥却自豪地说:“八尺门海堤开建了,孤岛很快就可以变半岛,下次你再来,天堑变通途,就不用坐船了。还有啊,几年下来,东山比咱太行山还绿了,那些树四季不落叶呢!”
河南林县那头的太行峡谷山多田少,相距不远的山西长治却有大片农田山田。谷文德曾想举家迁到长治去,希望当官的哥哥能帮助通融一下。谷文昌却说:“你是党员,又是村干部,得通过两边党组织批准,我无权过问。”
各奔东西一年多,1963年夏天的一个傍晚,谷文昌在办公室里久不下楼吃饭。儿子上去叫他时,却见他一个人面对窗口泪流满面,接过父亲手头的电报,才知奶奶去世了。此时的东山,正逢大旱,繁忙的工作使谷文昌忠孝难以两全。他速速汇了钱帮助安排后事,又忍着悲痛投身到抗旱指挥工作中了。
母亲走后那些年,谷文昌依旧每年给弟弟寄钱寄物。他知道,弟弟夫妇都是农民,又要抚养7个孩子,负担重。弟弟也知道哥哥负担不轻,5个孩子不管是亲生的还是抱养的,哥哥都一视同仁,连着嫂嫂娘家的亲人,得如何勒紧裤腰带啊。可是哥哥宁愿自己“瓜菜代”,也要时时接济他。
五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谷文昌难得地回了一次河南老家,给父母扫墓,看望乡亲们。
接到哥哥时,弟弟开玩笑似的提醒:“哥啊,你都当局长了,也该有套像样的衣服啊。”
哥哥则笑指身上有补丁的衣服说:“这不是挺好吗?我们是人民公仆,是干革命的,过分讲究穿着,就脱离群众了。”
林县不少人都记得谷文昌的这次还乡,别说吃穿住行与村民无异,还因为带的衣物不多而受冻了。林县人还记得,谷文昌南下后不仅把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工具介绍到福建东山,也把南方的好经验传播到林县。身在东海之滨,时时不忘太行山,在困难时期曾多次给家乡人民物资支援。
1981年1月下旬,谷文德接到哥哥召唤的消息,急急赶到闽南漳州医院时,顿时呆住了:病床上那个形销骨立、肤色黧黑、白发满头的人,是自己日思夜想的胞兄吗?哥哥不过65岁,一向精力充沛,怎么就病危了?眼前的一切,让他忍不住放声大哭。
积劳成疾的谷文昌,是在一次会上倒下而被“赶到”医院里来的,一检查,已是癌症晚期。受着病痛折磨的他,看着床前的弟弟,近乎喃喃自语:“莫哭莫哭,是人总有这一天。哥也没什么留给你的,床头这收音机,还有你看得上的衣物,就带回去留个念想吧。”
谷文德哭道:“我不要你的收音机,我也不要你的衣物,我就要哥好好的。你知道,这些年我除了那次想迁入山西和老娘、大哥做伴,还有那双皮鞋,我从没向你开口要什么。我真的什么也不要,就要哥哥快点好起来,再回老家,乡亲们都等着你回去呢!”
“哦,要求都没满足你,不怪我吧?”弟弟迁户山西之事,老家林县那边首先不放,说谷文德的村干部当得好,受到群众拥护。至于皮鞋,是东山驻岛部队发给兼任政委谷文昌的,但他从来不穿,而且宁愿给了警卫员也不给弟弟,只怕弟弟穿上皮鞋后自觉高人一等而脱离了群众。
“不怪,一点都不怪,我也是党员,哥说得对……”谷文德泣不成声。
谷文昌告诉弟弟,送他的这个收音机不是公家配的,是自己出钱买的:“这个收音机可以让人了解许多大事,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老家那边可能还稀罕……”
“你和老家那边的亲戚,不要怪我没帮上你们,共产党员不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大家都得自力更生。你回去代哥给咱爸咱妈上一炷香,也告诉乡亲们,就说咱没给他们丢脸……”
相比离别太久的故乡,谷文昌更放不下东山。这个海岛曾是那样的陌生,环境是那样的恶劣,现在却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他从1950年到1964年,从35岁到49岁,向这个海岛献上了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如果还有来生,他真愿意与这片土地长相守。
“我喜欢东山的土地、东山的人民。我在东山干了14年,有些事情还没有办好。我就不留骨灰了,都撒在东山吧,让我和东山永远在一起!”谷文昌的声音非常低,断断续续,几乎就只是口唇的气息。他似乎早有打算,流云潭影,来去无踪,只想化作春泥护花树。
床边的谷文德已是满脸泪水,眼前这个人,不仅是自己的二哥、谷家的次子,更是共产党员谷文昌!
六
回到林县的谷文德,带着儿孙们来到了著名的红旗渠,告诉他们:1960年,林县人民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在太行山上劈山凿就红旗渠。那个时候,谷文昌带领东山人民“上战秃山头,下战飞沙滩,绿化全海岛,建设新东山”已见成效,并在东山建成红旗水库,移山填海建海堤——林县与东山远隔千里,但不同的地方,一杆红旗一样的迎风飘扬。
虽然哥哥身上总有不少地方让做弟弟的不理解,甚至有怨气,但慢慢也就消解了。谷文德觉得哥哥行得正,是党的好干部。哥哥离世那些年,他“心悲兄弟远,愿见相似人”,期冀身边的干部们也有哥哥“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的样儿。
1991年5月,福建省委作出“开展向谷文昌同志学习”的决定。谷文德知道了哥哥是党和人民认定的好干部,为之深深自豪,却从不利用哥哥的影响力来为自家谋私利。数年后,谷文德也去世了,去世前留下遗言,要带上哥哥所留的一件遗物,并叮嘱兄弟三人的子孙:“谷家子弟都要好好做人做事,不要玷污了谷文昌这个名字!”这对连枝带叶的同胞兄弟,生生死死都手足情深。
2009年,谷文昌入选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评选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福建东山建起了“谷文昌干部学院”……
今日,走上福建东山岛,这里已是旧貌换新颜。昔日的荒沙滩、赤山岗,早已变成了国家海滨森林公园;昔日的风吹石走,满目苍凉,如今已是一步一景,如诗如画。美丽的东山岛,记录下一段“誓把荒岛变绿洲”的峥嵘历史,也深深印刻着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如磐初心与高尚精神。
本文来自【人民日报客户端】,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及传播服务。
谷文昌的兄弟情
来源:人民日报
图为东山岛风景。胡东雄摄
一
1949年初的太行山,峡谷里的树大都光秃了,仍有几片红枫在枝头漫舞,抖擞着精神,像要与寒风再斗三百回合。
原平原省林县(今河南省林州市)石板岩乡郭家庄一处农家,烤红薯香味四溢。农民谷文德出口的话,却显得有几分苦涩:“哥啊,你为何要自愿报名……”
他们说的是家事国事天下事。这年元旦,毛泽东同志借新年献词发令“将革命进行到底”后,“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激昂口号,连同中共中央关于从老解放区选调5.3万名干部,分配到新区领导建设的决议,在太行山谷里回响时,在林县当区长的谷文昌二话不说就主动报了名。
“文德,今年必将是中国历史翻天覆地的一个分水岭,关键时刻,共产党员更应当听从党的召唤!”谷文昌烤着火,说得热血沸腾,像报名时那样,字字铿锵。
“不是说自愿嘛!”
弟弟的话,弦外之音不言而喻。大哥早已前往山西谋生落户,他着实舍不得二哥谷文昌再远行。更何况二哥留在家乡做事,全家人还能经常见面。
33岁的谷文昌这个时候正值上有老下有小。母亲年逾六旬,在当石匠的父亲去世后备尝艰辛,身体一直不好,他南下的话必然难以尽孝;两个女儿大的不到10岁,小的还在咿呀学语……解放了,分田了,日子一天好过一天,祖祖辈辈梦想中的好日子刚开头,何必离家千里再奔波呢?
谷文昌说:“县委马书记、组织部蔡部长都带头报名南下哩。人家背井离乡来林县领导咱们闹革命,解放咱们之后又要随军南下,这是榜样哩!咱是共产党员,不能光顾自己,也要为党尽心,为江南老百姓的解放出份力!”
这番话如同钢钎凿石,弟弟的心扉终被撞出了火花,他知道哥哥有着比太行山巉岩还刚的犟劲、比峡谷云天还高的理想。想到亲如手足的兄弟情分,他为哥哥的壮志远行送上了定心丸:“好,你放心去吧,家里还有我!”
谷文昌就这样填写了“南征政民工作人员登记表”,在“家庭有啥困难”一栏里填上“没有困难”,在“家庭照顾的依托人姓名”一栏里写上“依托兄弟谷文德”。继而又联合6人向组织递交了一份写在烟盒背面的“保证书”:“每人家庭早有准备,不会拖后腿。阴历正月初九早饭集中十区署,保证当天下午报到平房庄。”
那晚给老娘洗过脚捶过背,第二天一早给小女梳过头后,谷文昌就打起背包,出现在了郭家庄的欢送会上。他在会上郑重表态:“我已下定决心,不解放江南老百姓誓不回来!决不给家乡丢脸,决不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
谷文德哪能知道:他的哥哥历时大半年、从中原腹地长驱3000公里,风雨南下,九死一生。躲敌机空袭,避特务黑枪,掩埋起战友的遗体又奋力向前。铁路遭敌破坏后,就靠双腿走路,滑倒了再爬起,血泡溃烂,脚底鲜红的肌肉与鞋底黏在一起,军装上印出一片白花花的盐渍。途中肺病发作,又经酷暑暴雨,高烧纠缠不休……
他更不知道,哥哥这一次远行,从体魄到灵魂都得以脱胎换骨,在进军福建途中所说的“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成了他一生践行的誓言。
二
福建在哪里?福建是什么样的地方?
1949年6月,谷文昌所在的长江支队到苏州后,才知并非留在苏州、上海,也不是拐个弯去大西南,而是继续南下去福建。明确最后的去向后,有人找来地图一看,不觉惊叫起来:福建偏远不说,连根红线(指铁路)也没有呀!有人还去书店买来相关图书,介绍福建的顺口溜很快就传开来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
不切实际的故事越说越玄,越说越使北方人犯怵。有人瞻前顾后,心里打鼓;有人犹豫不决,称病要求留在苏沪。谷文昌却一往无前,党指向哪,他就奔向哪。
接到兄长报平安的信后,谷文德便对福建省东山县那个海岛心心念念起来。1952年,他带着大侄女一路向东行,去看望据说已当了东山县县长的哥哥谷文昌。
几天几夜的火车,再换乘汽车,辗转来到东海之滨。从八尺门海峡坐船跨海,海浪颠簸得他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要是船能掉头,天边那个岛他可能就不去了。他想,一母同胞,哥哥在这孤岛进进出出,得吐多少回呢?
出现在眼前的县长哥哥,脚蹬布鞋,身着褪了色的灰中山装,绝非他在老家乡下所想象的“呢子大氅叫备用,迎来送往不发愁”的干部形象。那时候,哥哥在东山县当县长,嫂嫂当县妇联主任,所谓的家,就是在县长办公室里搭个床铺。他来了,只能和县委通讯员同挤一个门窗吱嘎作响的房间。
未见过大海的谷文德,幻想过东山的海岛风光,见到的却是个风沙呼啸的荒岛,心底竟有几分不信。晚上听得狂风呼啸,所居之屋就像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小舟,随时都会被风浪吞没,便问同住的县委通讯员:“你们这里的风沙咋这么厉害?”
通讯员回答他:“这还不算大,大的都能把房子整个给埋了。”
谷文德在东山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坐卧不安了,忍不住跟哥哥抱怨:“咱林县够艰苦了,没料到东山更苦!咱林县再苦,好歹树上叶子能吃,地里有野菜能挖,河里有水能喝。东山却到处光秃秃的,沙子能吃吗,西北风能吃吗,海水能喝吗?”
哥哥却说:“咱离乡背井不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吃上饭吗?共产党人不就是来救穷人的吗?”
来一趟不容易,哥哥和嫂嫂都希望他多住几天。可谷文德实在待不下去,别说海岛上无处不在的海腥味让他反胃,出门还得戴风镜,否则只能让风沙把眼睛打肿打痛。他感到难以适应,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风沙啊,怪不得东山的百姓称之为“沙虎”“风妖”!离开东山时,他带走了些小鱼干和虾米,带上了哥哥节衣缩食省下的一点钱。他觉得东山的条件太恶劣,能够建成哥哥说的美丽与富饶的地方吗?
三
谷文德回去不久,就听说东山发生了一场大战。如何个震惊世界,他不知道,只是听说毛主席表扬这是个大胜利,而且最欣慰的是,哥哥还活着!
新中国成立后,福建还一直是前线,与台湾一水之隔的东山更是最前哨。谷文德又开始为哥哥牵肠挂肚,没过几年,他又来到东山。
这次,他从老家带来了哥哥打小爱吃的山楂、杮饼。哥哥烟不离嘴,吃这些可以化痰,他一直都是关心哥哥的。他也照哥哥的吩咐,带来一把卸了柄的锄头,问:“你都当县委书记了,还要这把式干什么?”
谷文昌憨憨地笑着:“老家的锄头我从小用得顺手,今后走到哪里都带上它,既能就地劳动,也好提醒自己别忘本。”
谷文德握了握哥哥的手,伤痕累累,比自己的手还粗糙。
在和通讯员及东山干部群众闲谈中,他已然知道,哥哥这双手,攀过沙丘,打过石子,筑过堤,种过草,植过树,捏碎过一个又一个天大的困难!哥哥还雄心勃勃地发起了改造自然的造林治沙之战,屡败屡战,听说还当众立下誓言:“不把风沙制服,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样的官当得可真是苦,何必呢?他有不解,也有担忧。
但他又看到,与自己第一次登岛不同,东山变样了,不说昔日充斥于耳的风沙咆哮声变弱了,时歇时续了,水贵如油及燃料紧缺的现象也不再让人揪心。最引人注目的是,原来的濯濯童山、千里荒滩有了丝丝绿意。人在东山,其实也难见哥哥的身影,他不是下乡调研去了,就是在开会,要么是在参加劳动,终日不得闲。有天难得在饭间多唠几句嗑,雷声忽至,哥哥二话不说披上雨衣,拿起锄头就冲出了门。他从此知道,在这个地方,雷声就是造林的命令,雷声一响,“一呼百应”。他有次跟着侄儿冒雨奔向就近的植树造林战场,嗬,从四面八方向雨阵中奔来的,是无数的群众和学生,几乎人人都没穿鞋。谁都说:谷书记就在前面和大家一起种树哩!
谷文德感受到了哥哥在东山的威望,却也没忘记老母亲希望哥哥回故乡工作的愿望。回家前,他特地央求过兄嫂:“咱妈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来不了东山,你们干几年调回老家,不是一样为人民服务嘛,顺道也满足咱妈的一个念想……”
哥哥打断了弟弟的话:“当了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就是四海为家,听从党的安排,不管落在什么地方,都要在那里生根开花。你也入党了,该明白这个道理。”
那一次,哥哥陪着弟弟来到月光下的海边,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文德,你回去告诉咱妈,等东山像咱林县一样密密麻麻地长满了树,我一定回去好好服侍她老人家。你说中不中啊?”
月亮朗朗地照着兄弟俩。谷文德看见月光和海水一同在哥哥的眼里打转,闪烁得让他鼻子发酸。
四
谷文昌也不是忘情之人。那年观看潮剧经典戏《四郎探母》,戏里杨四郎有心过营探母,奈何关口阻拦,只能仰天长叹:“高堂老母难叩问,怎不叫人泪涟涟。”台下的谷文昌听得泪水直流,哽咽着对妻子说,不知道咱妈现在情况如何?
谷文昌真是有心把母亲接到东山来养老,但风烛残年的老人无法远行,只好节衣缩食接连寄钱寄物,有时让孩子们寒暑假回老家代为尽孝。
1962年2月中旬,谷文昌到北京参加大会,会后在回福建路上拐往大哥一家移居的山西长治市牛村,看望在这里过年的母亲。正值春节期间,他事先交代妻子带上孩子们从东山前来会合,弟弟也带着家小前来团聚。四代同堂,特地拍下了唯一一张家族合影。谷文昌夫妇和母亲住了一个来礼拜的窑洞,每晚都给老娘洗脚,听老人絮叨。
谷文昌欢迎亲人们去东山参加植树造林。弟弟心有余悸的不是苦和远,而是晕船,哥哥却自豪地说:“八尺门海堤开建了,孤岛很快就可以变半岛,下次你再来,天堑变通途,就不用坐船了。还有啊,几年下来,东山比咱太行山还绿了,那些树四季不落叶呢!”
河南林县那头的太行峡谷山多田少,相距不远的山西长治却有大片农田山田。谷文德曾想举家迁到长治去,希望当官的哥哥能帮助通融一下。谷文昌却说:“你是党员,又是村干部,得通过两边党组织批准,我无权过问。”
各奔东西一年多,1963年夏天的一个傍晚,谷文昌在办公室里久不下楼吃饭。儿子上去叫他时,却见他一个人面对窗口泪流满面,接过父亲手头的电报,才知奶奶去世了。此时的东山,正逢大旱,繁忙的工作使谷文昌忠孝难以两全。他速速汇了钱帮助安排后事,又忍着悲痛投身到抗旱指挥工作中了。
母亲走后那些年,谷文昌依旧每年给弟弟寄钱寄物。他知道,弟弟夫妇都是农民,又要抚养7个孩子,负担重。弟弟也知道哥哥负担不轻,5个孩子不管是亲生的还是抱养的,哥哥都一视同仁,连着嫂嫂娘家的亲人,得如何勒紧裤腰带啊。可是哥哥宁愿自己“瓜菜代”,也要时时接济他。
五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谷文昌难得地回了一次河南老家,给父母扫墓,看望乡亲们。
接到哥哥时,弟弟开玩笑似的提醒:“哥啊,你都当局长了,也该有套像样的衣服啊。”
哥哥则笑指身上有补丁的衣服说:“这不是挺好吗?我们是人民公仆,是干革命的,过分讲究穿着,就脱离群众了。”
林县不少人都记得谷文昌的这次还乡,别说吃穿住行与村民无异,还因为带的衣物不多而受冻了。林县人还记得,谷文昌南下后不仅把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工具介绍到福建东山,也把南方的好经验传播到林县。身在东海之滨,时时不忘太行山,在困难时期曾多次给家乡人民物资支援。
1981年1月下旬,谷文德接到哥哥召唤的消息,急急赶到闽南漳州医院时,顿时呆住了:病床上那个形销骨立、肤色黧黑、白发满头的人,是自己日思夜想的胞兄吗?哥哥不过65岁,一向精力充沛,怎么就病危了?眼前的一切,让他忍不住放声大哭。
积劳成疾的谷文昌,是在一次会上倒下而被“赶到”医院里来的,一检查,已是癌症晚期。受着病痛折磨的他,看着床前的弟弟,近乎喃喃自语:“莫哭莫哭,是人总有这一天。哥也没什么留给你的,床头这收音机,还有你看得上的衣物,就带回去留个念想吧。”
谷文德哭道:“我不要你的收音机,我也不要你的衣物,我就要哥好好的。你知道,这些年我除了那次想迁入山西和老娘、大哥做伴,还有那双皮鞋,我从没向你开口要什么。我真的什么也不要,就要哥哥快点好起来,再回老家,乡亲们都等着你回去呢!”
“哦,要求都没满足你,不怪我吧?”弟弟迁户山西之事,老家林县那边首先不放,说谷文德的村干部当得好,受到群众拥护。至于皮鞋,是东山驻岛部队发给兼任政委谷文昌的,但他从来不穿,而且宁愿给了警卫员也不给弟弟,只怕弟弟穿上皮鞋后自觉高人一等而脱离了群众。
“不怪,一点都不怪,我也是党员,哥说得对……”谷文德泣不成声。
谷文昌告诉弟弟,送他的这个收音机不是公家配的,是自己出钱买的:“这个收音机可以让人了解许多大事,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老家那边可能还稀罕……”
“你和老家那边的亲戚,不要怪我没帮上你们,共产党员不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大家都得自力更生。你回去代哥给咱爸咱妈上一炷香,也告诉乡亲们,就说咱没给他们丢脸……”
相比离别太久的故乡,谷文昌更放不下东山。这个海岛曾是那样的陌生,环境是那样的恶劣,现在却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他从1950年到1964年,从35岁到49岁,向这个海岛献上了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如果还有来生,他真愿意与这片土地长相守。
“我喜欢东山的土地、东山的人民。我在东山干了14年,有些事情还没有办好。我就不留骨灰了,都撒在东山吧,让我和东山永远在一起!”谷文昌的声音非常低,断断续续,几乎就只是口唇的气息。他似乎早有打算,流云潭影,来去无踪,只想化作春泥护花树。
床边的谷文德已是满脸泪水,眼前这个人,不仅是自己的二哥、谷家的次子,更是共产党员谷文昌!
六
回到林县的谷文德,带着儿孙们来到了著名的红旗渠,告诉他们:1960年,林县人民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在太行山上劈山凿就红旗渠。那个时候,谷文昌带领东山人民“上战秃山头,下战飞沙滩,绿化全海岛,建设新东山”已见成效,并在东山建成红旗水库,移山填海建海堤——林县与东山远隔千里,但不同的地方,一杆红旗一样的迎风飘扬。
虽然哥哥身上总有不少地方让做弟弟的不理解,甚至有怨气,但慢慢也就消解了。谷文德觉得哥哥行得正,是党的好干部。哥哥离世那些年,他“心悲兄弟远,愿见相似人”,期冀身边的干部们也有哥哥“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的样儿。
1991年5月,福建省委作出“开展向谷文昌同志学习”的决定。谷文德知道了哥哥是党和人民认定的好干部,为之深深自豪,却从不利用哥哥的影响力来为自家谋私利。数年后,谷文德也去世了,去世前留下遗言,要带上哥哥所留的一件遗物,并叮嘱兄弟三人的子孙:“谷家子弟都要好好做人做事,不要玷污了谷文昌这个名字!”这对连枝带叶的同胞兄弟,生生死死都手足情深。
2009年,谷文昌入选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评选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福建东山建起了“谷文昌干部学院”……
今日,走上福建东山岛,这里已是旧貌换新颜。昔日的荒沙滩、赤山岗,早已变成了国家海滨森林公园;昔日的风吹石走,满目苍凉,如今已是一步一景,如诗如画。美丽的东山岛,记录下一段“誓把荒岛变绿洲”的峥嵘历史,也深深印刻着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如磐初心与高尚精神。(钟兆云)
《人民日报》(2021年04月27日 第20版)
走进白水系列——郭家庄
白水是个美丽的地方,山青水秀,田园肥沃,人杰地灵,历史十分悠久。滚滚泾河伴着312国道穿境而过,寺山仰韶文化遗迹闻名遐迩。这里既有共工老祖的传说,又有红军长征路上英勇战斗的红色故事。
白水村共管辖六个社,最西头的是白水六社又叫郭家庄(过去也叫白水六队)。庄名来源已久,源于郭姓族人在此居住而得名。随着历史变迁、环境变化,目前庄内已无郭姓人口,据说姓郭的早已全部搬到陕西去了,只留下了庄名。郭家庄目前主要姓氏有张姓约占30%,唐姓约占20%,窦姓约占15%有20多户100多人。据庄中老人说,刘姓是后来最早定居此地的移民,从草峰塬搬迁到此地。而窦姓和丁姓则来源于打虎村。其更早应该是从陕西、河南等地移民至白水而来。
从姓氏发源来看,郭姓源于姬姓。西周时期,武王封其叔虢仲于陕西宝鸡,称西虢国(虢通“郭”)。又说:郭,外城,古代在城墙外围加筑的一道城墙。居于外城的遂以为郭氏,也有以居城郭不同方位而姓东郭、南郭、西郭、北郭,其后代多改姓单姓郭氏,这类郭姓主要发生在先秦时期的北方地区。
从家谱记载来看,张姓氏族最早活动于今河南濮阳和河北清河一带。直至西周宣王时期,在陕西地区出现了张姓的踪迹,秦汉之际进入甘肃。
据《姓氏考略》及《世本》所载,周成王改封自己的弟弟叔虞为唐侯,家族遂以唐为氏,又据《三国志·郭淮传》所载,今属甘肃省古羌人中有唐姓者。传说人文始祖黄帝亦是羌人。
窦姓起源古老,远祖始于夏朝。是大禹的后代,窦氏族人大多尊奉少康为得姓始祖。另外,在史籍《魏志》中,记载有库狄宥连部,其实就是氐族的一支比较强大的部落。以所居之地“屋窦城”为姓氏,称窦羽泥,族人主要分布在今陕西、甘肃一带。
丁姓源于姜姓,出自姜太公之子姜伋的谥号,属于以先祖谥号为氏。据史籍《元和姓纂》、《万姓统谱》、《通志·氏族略》等资料记载,丁氏源出姜太公之子伋,史称丁氏正宗。
据史记《汉书》、《通志·氏族略》和《中国姓氏》所载,刘姓的起源主要最早的一支来源于祁姓。刘累生于夏朝后期精通养龙技术,为夏朝第十三帝孔甲驯养4条龙,因而被孔甲赐姓为御龙氏,后来刘累的子孙以刘累的名字为姓氏,就是中国最早的刘姓。
郭家庄半山腰有山神爷庙一座,年代久远。外面是房、内是窑洞,土木结构。每年庙会期间,香客众多。前些年在庄中贤达人士呼吁下复建庙宇,民俗文化得到了保留。在老人记忆中,庄里古迹还有碑子坟,石碑约二米多高,一米宽,布满字迹,最为特别。后来毁于非常时期。
从地理位置来说,郭家庄位于大堡山脚下东侧一带,西临打虎村,东接白水四社,北与白水焦庄村隔河相望。距离白水街道约三里路程,距离寺山上文化遗址约二里。如果从庄内步行攀爬到大堡山顶,约需四十分钟。因为路程较近,过去庄内德高望重的窦浩贤老人曾在大堡山庙宇任老会长三十多年,亲自参与管理,由打虎村赵大师和唐师负责修建大堡山庙宇,玉皇爷楼子、黑虎灵官、八大金刚,大小十几间庙。出工出力,付出甚多。解放前窦浩贤担任乡职期间,凡是有自然灾害时,庄里群众一律免交粮税,深得百姓拥护,威望很高。
大堡山也叫龙凤山,是东川第一高山,古代亦是重要的烽火台。人们常说:“有山必有仙,有仙必有凤。”在民间来说,大堡山是神山,所以自然会引来凤凰。传说山顶有远古观象台遗迹,和大陈村凤凰山一南一北遥相对应。陇山周边,泾河流域,以龙或者凤命名山,由来已久,无不说明文化历史的源远流长、山势的奇峻高大以及山川之间沟壑纵横,峁塬相连。千年以来,龙文化较为盛行,基本上一些较大的村庄都有龙王庙。在农耕时代,祈求风调雨顺是农民最大的期望。尤其是陇东黄土地上,生活是很艰苦的,以往是,现在还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永平指出历史上月氏道就位于白水到黄寨一带,实属南来北往交通要道,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
郭家庄坐南向北,庄南靠山,有中山、唐家山、西沟山、赵家湾、阳洼,长沟垴,老瓦厂,滩洼,猩猴咀。沟有大沟,罗沟。和白水四社以“乱峭洼”为界,“乱峭洼”在近代及以前,多为埋葬在战乱中丧生的人。郭家庄在过去一度由打虎村管理,学生上学在打虎小学念书。后来赵国华任支书的时候,郭家庄改为星光大队(现白水村)管理,学生改为白水小学和白水中学念书。当时,郭家庄有羊三圈,还有电话,所以农民戏称为“小台湾”。想当年,郭家庄人依山选好地形,修成崖面,在上面凿窑,然后安装木门窗,稀泥抹墙。黄土窑洞,一般高3—4米,宽2.5—3米,深3—10米,有的更深。俗称“土窑,锅头连炕,烟囱朝上”。窑洞最显著的特点是冬暖夏凉。清时惠登甲曾写诗赞曰:“远来君子到此庄,休笑土窑无夏房。虽然不是神仙洞,可爱冬暖夏天凉。”
郭家庄交通便利,亦是国道重要节点。清代民国期间,左公柳沿着庄中大道两边矗立,犹如交通的指向标志。看到树,就意味着有路,有人家。驼铃叮叮当当,车轱辘吱吱咛咛。在过去,人们到白水跟集,只有步行至白水西门,哪怕是小脚老太婆也不例外,约需要20分钟才能到达城门。白水原名泉驿,是丝绸古道必经之地,旅客云集,西上之车马络绎不绝,东来之驮骡绵绵不断,过路人看中的是此地的车马店、饭菜和水源。白水城墙高大,西门、东门特别宽敞,约有三层楼高。城门里大车随意可过,城门上有两间房宽,建有土地庙一座,以护佑白水子民出进平安、四季风调雨顺。假如城墙完整保存下来,定是西北无价之宝。
一九三五年,红二十五军长征路过白水,在大堡山附近与敌人发生激烈战斗,期间红军在大堡山东侧余脉俗名叫鳖盖墚的小山峁狙击敌人,鳖盖墚周围挖有一圈战壕,近80公分宽。敌人在郭家庄曾设有指挥部,由山下往大堡山顶连续强攻。留宿期间,在村民家里曾留下了半个葫芦头,也就是葫芦制作的舀水用具。徐海东指挥红军在雨中共消灭一个营的敌军,剩余之敌落荒而逃。伤员就地在打虎村和郭家庄农民家中治疗、修养。郭家庄窦鹏诚曾救治一名受伤的红军战士,马家队伍严查期间,窦鹏诚以是外地来的叫花子、要饭的蒙混过去,红军战士伤好后上北塬回归陕北。解放后曾来郭家庄叫窦鹏诚出去上班,因为家里老人尚在,故没去。由此,在郭家庄留下了红军的足迹,也得到了红色精神的熏陶。二十多年前,在郭家庄山上和田地里曾陆续发现旧时战斗中用过的空子弹壳。这是红军在崆峒区唯一进行的一场斗争,并且取得了战斗胜利,所以龙凤山(也叫大堡山)又名胜利山。目前,山顶立有红军长征战斗胜利纪念碑一座,每年都有好多人到白水镇胜利山追寻长征足迹,瞻仰英雄事迹,学习红色精神。
解放前后,郭家庄有200多口人,主要是居住在山脚下或者半山腰的窑洞。西沟和大沟万寿宫下皆有泉水一眼,从石头缝隙流出,一年四季水汪,水质优良,清甜可口,满足了全庄人吃水之用。知识青年下乡时期,兰州大学白教授等人曾用石块修固过水泉。郭家庄山上有土夯的高大堡子,旧社会曾用来躲避匪乱。白水郭家庄抗战时期挖的地道有三十多米长,有两条地道口,老人们都叫窨子。特殊时期,庄里人在老窖洞里的小地窖藏粮食,以备急用。传说山上有个约四米深的胡圈,曾经发现破损军械,全部上交给政府,可能是在大堡山战斗中遗弃的。过去,庄里有两个大带马车,多数时间用于农业生产,闲暇时间拉货,拉沙子和石子。
旧时官路基本依山脚下而修,左公柳沿路遍布,高大粗壮,绿意盎然,长长的官道成了致富路。庄中曾有一棵百年老梨树,结的果子为软梨,非常好吃,二个人合抱才能围住此树。在过去,郭家庄中的老先生有唐克勤,擅长画画,又懂中医能看病,宅心仁厚,高寿九十多岁。郭家庄老教师有丁心良、窦鹏真,丁俊南等人。郭家庄朱桂兰已80多岁,擅长剪纸,绣龙。以前,郭家庄有瓦窑一座,用工四人经营了十几年,生意红火,主要销售到04厂、泾川石油四分部以及附近村子。
在人们的记忆里,正月里白水村郭家庄春官诗说的最好,有铁嘴之美誉,大人小孩跟着社火听春官说。从60年代兴办社火开始,每年春节期间,看社火必看郭家庄的春官诗说唱,春官以王怀诚,张耀敏,张志兴,刘兴旺最为有名。
如今,郭家庄张志强老人虽已年迈,八十有余,但是精神矍铄,身体硬朗,记忆里强。老人入党六十多年,是庄里入党最早的人。和张世昌,张长录,潘桂英(女)等在队里(郭家庄)早期工作。其个人在队里工作时间长达二十多年,曾荣获平凉县先进生产者、先进个人等表彰奖励。
白水村郭家庄共有400多亩地,过去主要种植麦子、米子、高粱、也种过烤烟。目前主要种植玉米,约有200亩,推广地膜覆盖,保持土壤水分,增加亩产量。另外,种植西瓜有200多亩。山地基本退耕还林,使原来光秃秃的山变成绿水青山,改善了生态环境。目前,一个人平均有一亩多地。庄内有养殖户三家,经济效益可观。岁月如梭,时代变迁。过去,家家户户都用的是煤油灯,有煤油灯的地方是亮的,其他地方是黑的,早晨起床,满鼻子都是黑烟灰。六十年代起,郭家庄通上了电,从石磨子到电磨子,解放了劳动生产力,给电视机、洗衣机、家用电器的使用提供了方便。自来水通向每家每户,有些人家还接进了厨房,从此不用再去沟里担水吃了,尤其是下雨的时候,泥路湿滑,挑回来的水只剩半桶。此外,自来水还能解决家庭院子里种植蔬菜用水问题。庄子里外主要道路已铺水泥,彻底解决了下雨难行的情况,为小汽车、农用三轮车、摩托车、播种机,收割机行进提供了方便。改革开放以来,郭家庄窦曙光工程队成立后,带动了周边群众出门务工,增加了群众收入。经过一代代接续努力,以前贫困的人们,现在也能吃饱肚子、穿暖衣裳,有学上、有房住、有医保。全面小康、摆脱贫困。农业兴旺,瓜果满园,人民生活富足安康,农业播种收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不用再顶着烈日去人工收割、碾场等苦劳力活动了。教育昌盛,人才辈出。今朝家乡,更展新颜。随着社会发展,郭家庄在人们的口语中变成了“国家庄”,更接地气、也更大气了。
家乡之美,非言辞所能尽述;家乡之情,非笔墨所能描绘。铭记家乡白水之恩情,传承文化之精髓,共谋发展之大计。而今,白水村郭家庄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乡村振兴政策下,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幸福。
美好新时代,农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乡村振兴让农村更宜居,生活更幸福,画卷更优美。只有汇聚起推动乡村振兴的合力,才能建设更好的幸福美丽家园。
相关内容
相关资讯
-
【推荐】MCU火了源铄基金
2022年伊始,半导体又一细分赛道火了。不久前,32位MCU企业“航顺芯片”正式完成10亿元D轮融资,本轮由深投控、深创投、青岛海尔汇智、方广资本、康成亨资本、美格智能、中航基金联合战略领投。这笔融资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刷新了近期国内MCU领...
-
【推荐】500增强一箩筐指数增强基金该如何选000478基金净值查询
来源:银行螺丝钉的雪球原创专栏今天来介绍一个比较特殊的指数基金组合。是蛋卷开发的500增强基金一箩筐。这是目前比较好的一个“500增强基金如何挑选”的解决方案。
-
【推荐】4月5日起机票燃油费再下调单程最低降至30元油价最低能低到多少钱
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潘福达3月30日,记者从飞猪和去哪儿平台获悉,机票燃油附加费年内第二次下调,4月5日起单程最低降至30元。飞猪、去哪儿表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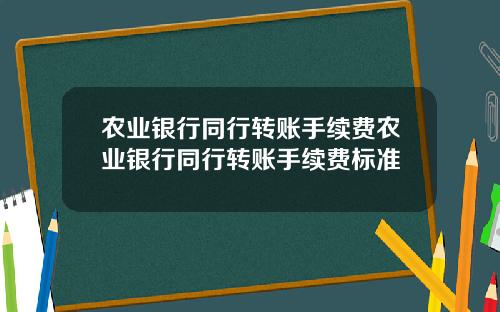 农业银行同行转账手续费农业银行同行转账手续费标准
农业银行同行转账手续费农业银行同行转账手续费标准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以下的问题,关于农业银行同行转账手续费,农业银行同行转账手续费标准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本文目录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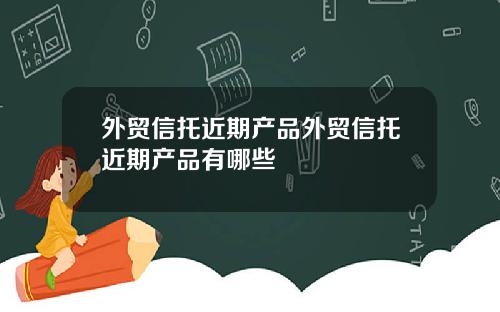 外贸信托近期产品外贸信托近期产品有哪些
外贸信托近期产品外贸信托近期产品有哪些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解答外贸信托近期产品这个问题的一些问题点,包括外贸信托近期产品有哪些也一样很多人还不知道,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析分析,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如果解决了您的问题,还望您关注下本站哦,谢
-
 国际层压板有限公司,国际板材
国际层压板有限公司,国际板材各位老铁们,大家好,今天由我来为大家分享国际层压板有限公司,以及国际板材的相关问题知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可以帮助到大家,还望关注收藏下本站,您的支持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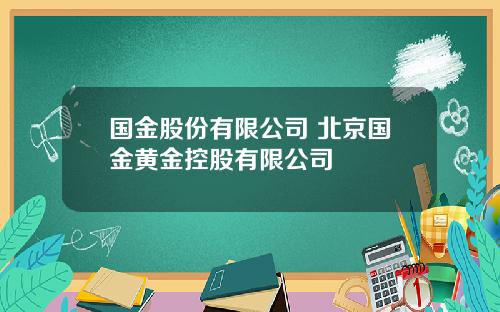 国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金黄金控股有限公司
国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金黄金控股有限公司大家好,今天给各位分享国金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些知识,其中也会对北京国金黄金控股有限公司进行解释,文章篇幅可能偏长,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

